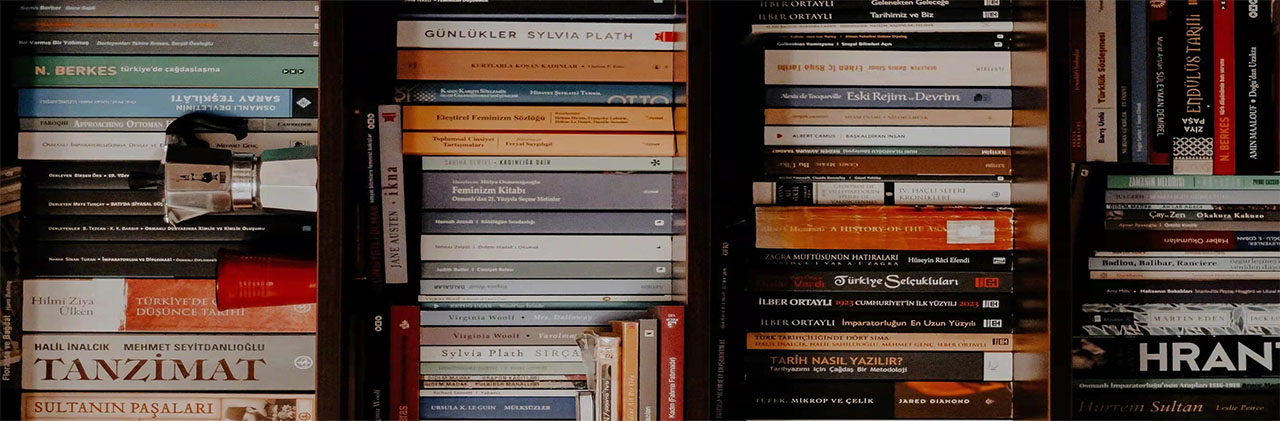
AIGC的可版权性——论中美司法判例的差异
上海天聿格律师事务所 柴玮杰
2022年底,OpenAI的大型语言生成模型ChatGPT刷爆网络。近年来,伴随着AIGC(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逐渐走入日常生活。豆包、文心一言、通义千问等国产AIGC日渐普及,利用AI进行文书写作、绘图已经越来越成为人们日常工作、娱乐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那么,随着AI技术的飞速发展,AIGC的逐渐增多,这些借由AI所制造的文章、图画是否能如传统人类作者独立完成的文字作品、美术作品一般地受到保护呢?如果能够的话,是以哪部法律进行保护?AIGC作品又是否属于当前《著作权法》中“作品”的范畴?
以下仅以中美两国目前对图画作品的不同司法判例进行讨论,从两国的异同来探究AIGC在图画作品领域的可版权性。
美国
1. 2023年2月21日,美国版权局就《Zarya of the dawn》注册事宜做出答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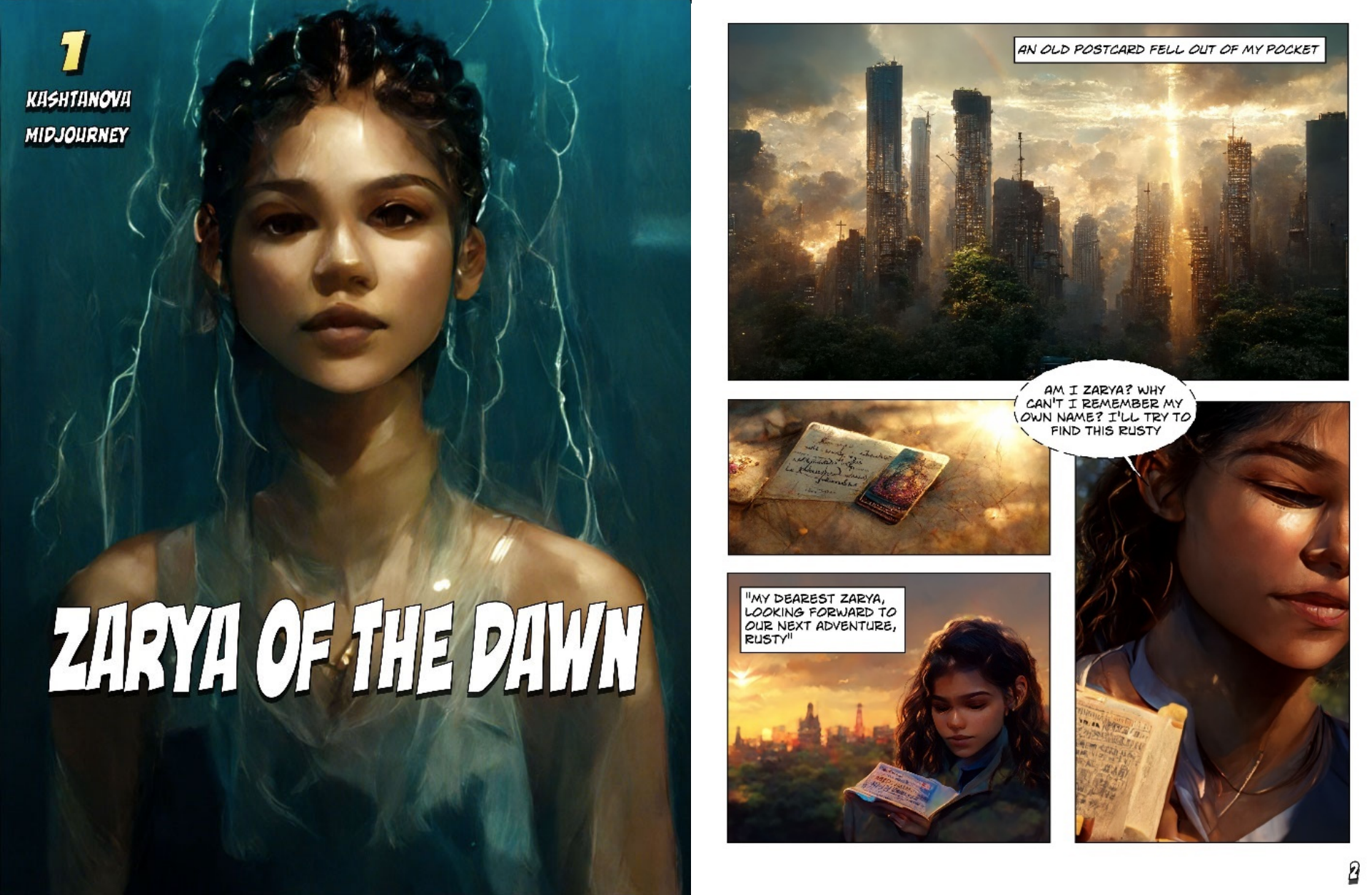
Zarya of the dawn
《Zarya of the dawn》是由Kashtanova创作的漫画作品,其中部分图画作品使用了AI软件Midjourne进行创作。在最初进行版权登记时,Kashtanova并未揭露该作品使用了Midjourne创作,版权局因此下发注册证书。后版权局通过社交媒体发现Kashtanova创作该漫画时使用了人工智能,因此认为此前颁发的注册证书存在错误,要求Kashtanova就该注册证书为何不应被撤销做出回复。
就Kashtanova律师做出的认为该作品可注册的回复,版权局于2023年2月做出了答复。
在该答复中,版权局承认作者Kashtanova对其作品在文字及图片元素的选择,协调和安排上的作者身份,并认同该等作者的身份应当被著作权法所保护。但版权局认为作品中由AI创作的部分应当声明放弃权利。版权局基于前述原因,将撤销此前对Kashtanova下发的注册证,并重新下发一个仅保护其本人所创作的作品的注册证。
首先,版权局主张,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仅是人类作者的作品。在Urantia Found. v. Kristen Maaherra, 114 F.3d 955, 957–59 (9th Cir. 1997).一案中,法院确认一本包含了由非人类的灵体所创作的文字的书仅可以在其存在人类的选择及安排的前提下才可以获得著作权的保护。灵体所创作的作品并非著作权法所意图保护的对象。
在此前提下,对于借由AI Midjourney所创作的单幅图画作品,版权局依据其自身的知识,Midjourney的公开文件资料做出如下分析及判断:
人工智能软件并不能将人类输入的提示词理解为某种用以创作特定表达的特定的指示。因为人工智能软件不能像人类一样理解语法,句子的结构或者单词。人工智能只是会将文字或词组转换为更小的单位,然后将之与其训练数据相比较,并创作出新的图画。如此,软件的使用者并不能提前预见人工智能软件将会依据其指示做出什么样的画作。整个作画的结果并不由人类使用者所控制。
基于上述原因,版权局认为由人工智能Midjourney创作的作品不受著作权法所保护。
相较于使用一种可控制的工具来画出理想中的画作,Kashtanova使用了一种她自己不可以预测的方式来生成图片。最高院在Burrow-Giles, 111 U.S. at 61一案中曾如此解释可受版权保护的作者,其应该为“实际形成作品的人”、作为创造或者策划者的人。
版权局认为,向人工智能输入提示词的人并非实际产生了图片 的人,因此并非图片的策划者。因人工智能产出的图片与使用者希望人工智能产出的图片之间可能存在差异,而使用者产生图片一事缺乏了足够的控制力。这也使得人工智能不同于其他由艺术家使用的作图工具。版权局认为使用人工智能更近似于以下的情况,即一名客户雇佣了一位艺术家为其作画,并向其做出了一些模糊概括的指示。很显然,在上述情况中,客户并不能作为作者。
基于上述理由,版权局认为对《Zarya of the dawn》的版权保护应当排除由人工智能创作的部分。
2. 2023年9月5日,美国版权局就《Théâtre D’opéra Spatial》注册事宜做出的答复。

Théâtre D’opéra Spatial
《Théâtre D’opéra Spatial》系Allen先生于2022年9月21日申请注册的二维美术作品。虽Allen先生并未主动披露该作品系由AI参与创作完成,但是由于该作品作为赢得2022年科罗拉多州博览会年度美术大赛的第一幅AI创作作品获得了全国性的关注,因此版权局亦注意到其系AI创作的事实。由于Allen先生拒绝声明放弃AI创作部分的版权,因此版权局拒绝了该幅作品的注册申请。
而对于Allen先生第二次申请版权局对此决定重新考虑(reconsideration)的要求,版权局做出了如下答复:
与前述《Zarya of the dawn》相同地,版权局在开篇即强调了版权法仅保护人类的作品。在Thaler v. Perlmutter一案中,美国哥伦比亚地方法院做出如下解释:
1976年法案明文要求…可注册版权的作品需要具有智力、创造性或艺术能力的创作者。主张版权的创作者必须是人类吗?答案是肯定的。
在分析人工智能作品时,版权局必须决定人类作者能否被认为是AI作品的创作者。在2023年的3月,版权局就AI创作的作品之注册提供了一份公共指南。指南中提到,在审核注册申请时,版权局必须考虑如下问题:
作品是否主要为人类创作,而电脑仅仅只是辅助工具?或者作品中的传统作者元素(文字,音乐表达或者选择,安排的元素等)是实际由人类而非机器构思并执行的?
如果一项作品的传统作者元素是有机器创作的,则该作品就缺乏人类作者元素,版权局就不会准予注册。
在版权局看来,《Théâtre D’opéra Spatial》人类作者Allen的在其中投入的行为不能使其成为该作品的作者,因其主要行为只是向人工智能软件Midjourney输入提示词。尽管Allen先生输入了624次提数次并进行无数次的修改,但是前述步骤都最终取决于人工智能软件如何处理Allen先生的提示词。
如版权局在其3月出版的指南中所述,“当人工智能技术只是收到来自人类的提示词,然后产生复杂的书面、视觉或音乐作品作为回应,‘作者的传统元素’是由技术决定和执行的,而不是人类使用者。”
基于前述理由,版权局认为Allen先生非《Théâtre D’opéra Spatial》的作者,如需在版权局登记该副作品,则人工智能创作的部分必须声明放弃权利。
值得注意的是,版权承认,在输入提示词的过程中,一些提示词可能存在创造性。一些提示词可能可以作为文字作品收到保护。
中国
1. (2019)京73民终2030号民事判决书-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菲林律师事务所通过使用威科先行数据库创作了《影视娱乐行业司法大数据分析报告》的文章,涉案文章针对各部分内容使用了曲线图、柱状图、圆环图等15张图形用于说明相关统计数据。
百度公司未经授权在其经营的百家号平台发表涉案文章,因此被诉侵犯菲林律师所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涉案文章中的图形部分是菲林律师事务所基于收集的数据,利用相关软件制作完成,虽然会因数据变化呈现出不同的形状,但图形形状的不同是基于数据差异产生,而非基于创作产生。因此,涉案文章中的图形不构成图形作品。
2. (2023)京0491民初11279号民事判决书-北京互联网法院

春风送来了温柔
原告使用开源软件StableDiffusion通过输入提示词的方式生成涉案图片,后将该图片以“春风送来了温柔”为名发布在小红书平台。2023年3月2日,被告未经原告许可,在百家号账号发布了名为《三月的爱情,在桃花里》的文章,该文章配图使用了涉案图片,且截去了原告在小红书平台的署名水印。
原告因此诉被告侵犯了原告享有的署名权及信息网络传播权。
法院审理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本法所称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 根据上述规定,审查原告主张著作权的客体是否构成作品,需要考虑如下要件:
1.是否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
2.是否具有独创性;
3.是否具有一定的表现形式;
4.是否属于智力成果。
本案中,从涉案图片的外观上来看,其与通常人们见到的照片、绘画无异,显然属于艺术领域,且具有一定的表现形式,具备了要件1和要件3。
从整个作品创作的过程来看,原告进行了一定的智力投入,比如设计人物的呈现方式、选择提示词、安排提示词的顺序、设置相关的参数、选定哪个图片符合预期等等。涉案图片体现了原告的智力投入,故涉案图片具备了上述第4点-“智力成果”要件。
就上述第2点的“独创性”要件,一般来说,人们利用StableDiffusion类模型生成图片时,其所提出的需求与他人越具有差异性,对画面元素、布局构图描述越明确具体,越能体现出人的个性化表达。
本案中,从涉案图片本身来看,体现出了与在先作品存在可以识别的差异性。从涉案图片生成过程来看,一方面,虽然原告并没有动笔去画具体的线条,甚至也没有百分之百的告知StableDiffusion模型怎样去画出具体的线条和色彩,可以说,构成涉案图片的线条和色彩基本上是StableDiffusion模型“画”的,这与人们之前使用画笔、绘图软件去画图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原告对于人物及其呈现方式等画面元素通过提示词进行了设计,对于画面布局构图等通过参数进行了设置,体现了原告的选择和安排。另一方面,原告通过输入提示词、设置相关参数,获得了第一张图片后,其继续增加提示词、修改参数,不断调整修正,最终获得了涉案图片,这一调整修正过程亦体现了原告的审美选择和个性判断。因此,涉案图片并非“机械性智力成果”。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认定涉案图片由原告独立完成,体现出了原告的个性化表达。综上,涉案图片具备“独创性”要件。
同时,法院认为,在上述人工智能模型出现以前,人们需要花费时间精力去学习一定的绘画技能,或者需要委托他人,才能获得一幅绘画作品。在委托他人绘画的场景下,委托人会提出一定的需求,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的需求动笔去画出线条、填充色彩进而完成一幅美术作品。在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一般来讲,动笔去画画的受托人被认为是创作者。这种情形与人利用人工智能模型生成图片的情形类似,但是两者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即受托人有自己的意志,其在完成委托人委托的绘画工作时,会在绘画中融入自己的取舍和判断。而现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不具备自由意志,不是法律上的主体。人们利用人工智能模型生成图片时,不存在两个主体之间确定谁为创作者的问题,本质上,仍然是人利用工具进行创作,即整个创作过程中进行智力投入的是人而非人工智能模型。
因此,涉案图片属于美术作品,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同时,涉案图片是基于原告的智力投入直接产生,且体现出了原告的个性化表达,故原告是涉案图片的作者,享有涉案图片的著作权。
对比分析
在(2019)京73民终2030号一案中,所涉及的图形仅仅是基于数据而产生的,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只要数据不发生变化,不同的使用者使用同一软件检索相同的关键词所产出的图形都是相同的。本质上来说,该案中的“图形”仅仅是数据的可视化反馈,并不涉及到传统意义上美术作品的领域。
而(2023)京0491民初11279号一案的涉案作品,更接近传统意义上的“美术作品”,为一名少女摸样的女孩的图片。从北京互联网法院对案件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中美两国在某些部分的分析是类似的。比如:
1. 均认定人工智能不能作为作品的作者,著作权法只保护人的作品。美国作为判例法国家,系从其以往的判例中得出的结论,能成为“作者”的只能是人类。 中国作为成文法国家,则是从法律的规定中得出的结论,即依据《著作权法》第十一条, 作者限于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人工智能模型本身无法成为著作权法上的作者。
2. 均认为,利用人工智能模型作为“工具”,与以往利用画笔,绘图软件绘图具有很大的不同。人类并无法决定人工智能作画的线条、色彩,从一定程度上说,图片可以说是人工智能画的。
3. 两国的法院/版权局在分析时使用了相同的类比,即利用人工智能绘画,非常类似于客户委托画家进行创作的情景。
但是,尽管存在部分近似的判断和分析,中国的法院与美国的版权局却导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中国的法院认可人工智能所做绘画的作者为软件的使用者,且认为该作品为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而美国的版权局却认为人工智能所参与绘制的部分不能够申请登记版权,不是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究其原因,美国的版权局更偏重人工智能作画的部分的不可控制性,认为由于其不受人类使用者的控制且不可预测,因此,虽然人类使用者进行了提示词的输入,但不能认为人类是该部分作品的“作者”。好比上述第3项提及的内容,美国版权局亦认为使用人工智能绘画类似于客户委托画家进行画画,但美国版权局得出的结论为,人工智能类似于其中画家的角色,为作品的实际创作者,因此人类使用者作为委托人,不能取得作品的作者身份。
而中国的法院更注重人类使用者在使用人工智能绘画时投入的智力因素,认为由于人工智能不具有独立意志,在其无法取得“作者”身份的前提下,虽然确实类似客户委托画家进行美术创作的情况,但本质人工智能仍为人类使用者作画的工具。不同的人输入不同的提示词、设置新的参数,就会成不同的内容。因此,图片体现出了使用者的个性化表达。
我们认为,中国法院的判决,应当暗含了法院鼓励公民使用人工智能进行创作,保护人工智能创作结果的指导思想。一如其在判决书中所言的:鼓励创作,被公认为著作权制度的核心目的。只有正确地适用著作权制度,以妥当的法律手段,鼓励更多的人用最新的工具去创作,才能更有利于作品的创作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在这种背景和技术现实下,人工智能生成图片,只要能体现出人的独创性智力投入,就应当被认定为作品,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尽管如此,仍不能规避的一个问题是,人工智能并不具备本身的意志,其所作出的绘画,仅是基于其数据库,针对人类输入的提示词和参数调整所作出的反馈。就同样的提示词,人类画家依据本身的经验,技巧会做出不完全相同的,具有个性化的画作,而同一个人工智能,在提示词相同的情况下,做出的图画作品是相同,或者至少是类似的。
相比于《Théâtre D’opéra Spatial》中高达六百余次的提示词修改,《春风送来了温柔》的文本输入及参数修改并不复杂,甚至可以说是较为简单的。
中国法院同样认为,“利用人工智能生成图片,是否体现作者的个性化表达,需要个案判断,不能一概而论”。输入的提示词及个人调整的参数,需要复杂到何种程度,才能被认为体现了作者的“个性化”表达,而使得其借由人工智能绘制的图画可以被著作权法所保护,依然是一个问题。
在此问题上,笔者更倾向于美国版权指南中的论述,即:在输入提示词的过程中,一些提示词可能存在创造性。一些提示词可能可以作为文字作品收到保护。
也就是说,即使以中国法院认可人工智能创作的绘画作品可以由人类使用者作为作者来受到保护的前提下,该种作品的文字提示词或者一连串的提示词也应当是具有创造性的,足以作为文字作品收到保护。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工智能绘画作品才能够说反应了人类作者“个性化”的表达,体现了人类使用者的创意而应当收到保护。只是由简单的“提示词”完成创作的作品,仅仅是人类使用者“思想”的体现,远远触及不到著作权法所要保护的具体的“表达”,因此并不应当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如果比较《Théâtre D’opéra Spatial》与《春风送来了温柔》,两幅作品在绘图的元素构成,复杂程度,细节的精致程度上均有着非常大的差异。
尽管复杂精致如《Théâtre D’opéra Spatial》,美国的版权局依然坚持必须声明放弃人工智能创作部分的权利(人类不能成为该部分的作者),而即使简单如《春风送来了温柔》,中国法院依然认为人类使用者可以作为整幅作品的作者主张权利。
两国的倾向之不同由此可见一斑。
结语
人工智能的普及和使用已经成为未来生活的大趋势,以后关于人工智能的相关申请及司法案件一定会越来越多。对于AIGC作品的可版权性问题,随着案件的增多,未来必然将迎来更多的讨论。后续两国在司法实践中是否会延续当前的标准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