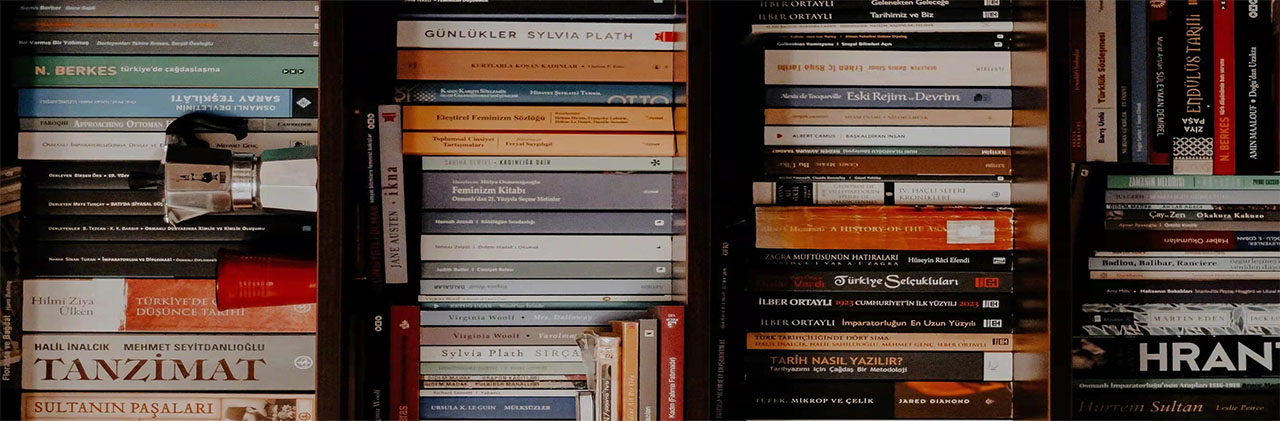
虚拟偶像是指以绘画、动画、CG等形式构建的,在互联网等虚拟环境中进行偶像活动的仿真偶像。近年来因虚拟偶像产生的法律纠纷和舆论争议频繁走入大众视野。尤其在2024年,苏州互联网法庭、杭州中院分别对“首例虚拟主播形象损失纠纷案”“首例虚拟数字人侵权案”作出宣判,更是引发业界对虚拟偶像人格权、知识产权和劳动法等相关的法律议题的深入探讨。本文将从虚拟偶像的种类和发展出发,对虚拟偶像相关的人格要素利用、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律问题,作出初步探索。
一、虚拟偶像的演进和种类
(一)虚拟偶像的诞生和发展
“虚拟偶像”一词最初于1990年诞生于一款名为《超时空要塞》的动画和同名游戏。由于其中的虚拟形象“林明美”广受欢迎,动画公司便以该虚拟形象为名义推出了实体专辑。“林明美”被称为“元祖虚拟偶像”。其后,虚拟偶像经历了几个个性鲜明的发展阶段。真正意义上的初代虚拟偶像是以“初音未来”“洛天依”为代表的“虚拟歌姬”。“虚拟歌姬”(VOCALOID)不再是简单的虚拟形象,它们以音源库和语音合成软件为基础,由用户输入内容形成歌曲和表演。如果说“虚拟歌姬”奠定了虚拟偶像以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的简写,即用户生成内容)为基础的商业模式。“虚拟主播”(VTuber)的出现则使虚拟偶像的这一属性更为增强。2016年,伴随着直播行业的兴起,以“绊爱”为代表的虚拟主播开始攫取流量并大火至今。如今的虚拟偶像的内容产出早已突破了歌曲延伸到歌舞表演、游戏直播、日常Vlog、剧情创作和营销带货等层面。需要说明的是,“虚拟偶像”一词在日常中常与“虚拟形象”“虚拟数字人”“虚拟人”“数字人”和“虚拟主播”等词汇具有相似含义,但本文讨论的仅是利用数字形象和数字技术开展类似真人偶像活动的狭义上的“虚拟偶像”。
(二)当代虚拟偶像的种类
回顾虚拟偶像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其每一次跨越性发展,都是由技术驱动的。当代虚拟偶像依托于语音合成、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人工智能和全息投影等数字技术制作而成。根据技术驱动比例的不同,又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 真人转化型
真人转化风格的虚拟偶像以当红明星的真人形象为基础,将真人偶像的形象体态和行事风格进行数字艺术转化,形成一个与真人偶像有明确对应性的虚拟“分身”,在电商平台、数字媒体等多种场合代替真人明星完成偶像活动。较为知名的有易烊千玺在“天猫”平台的分身“千喵”,这一虚拟偶像曾创造上线三天就破千万人气值的惊人业绩。
2. 真人扮演型
真人扮演风格的虚拟偶像是当今虚拟偶像市场的主流。该类虚拟偶像和“完全虚拟型”的虚拟偶像会预先设置一个基本的虚拟形象,即“皮套”。然后通过真人演员佩戴面部识别和动作捕捉设备将真人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转化为虚拟偶像的动态形象,这些演员被称为“中之人”。曾经红极一时的虚拟偶像女团A-SOUL便是其中的代表。
3. 完全虚拟型
完全虚拟风格的虚拟偶像与真人扮演型的主要区别在于人工智能技术的驱动比例不同。这类虚拟偶像完全由技术和算法驱动,并不依赖“中之人”。根据公开资料,腾讯推出的虚拟主播“艾灵”较接近这一类型。“艾灵”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深度学习,能够全天候不间断完成具备的唱歌、作词、书法和直播等活动。
二、虚拟偶像的人格要素利用
无论是哪种类型的虚拟偶像,都离不开对真人包含声音、肖像等形象元素甚至姓名的利用。从这个意义上看,虚拟偶像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主要通过“人格要素的商业利用”【1】实现价值转化的商业模式。以下简要介绍目前虚拟偶像行业人格要素的利用现状、法律挑战和因应之策。
(一)声音权益
虚拟偶像的打造是以“语音合成”为基础的。“声音”是虚拟偶像起源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是虚拟角色形象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受发展阶段和行业惯例的影响,虚拟偶像的偶像生产、同人创作、领域拓展等各环节广泛存在侵害声音权益的现象。例如,偶像生产环节的盗录和盗播,同人创作环节的非法采录、截取和加工,经营拓展环节的授权外使用以及深度伪造技术的滥用。【2】
我国民法典第1023条规定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参照适用肖像权的保护,明确将声音权益作为特殊的人格利益予以保护。在何某与微播视界科技纠纷案【3】中,法院认定涉案短视频构成对原告何某肖像及声音的侵害,明确肯定了自然人的声音权益。近期宣判的全国首例‘AI声音侵权案’进一步明确声音权益及于语音合成技术处理后的“声音”。法官指出,“我国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首次以立法形式将保护“声音”写入民法典,明确参照适用肖像权的形式保护自然人的声音,体现了对人格权益全面尊重和保护的立法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声音作为一种人格权益,具有人身专属性,任何自然人的声音均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对录音制品的授权并不意味着对声音AI化的授权,未经权利人许可,擅自使用或许可他人使用录音制品中的声音构成侵权。”【4】
司法实践中声音权益纠纷的凸显对行业的规范性提出了要求。音源使用方要取得权利人的知情同意和相应授权,授权协议的用途和范围要尽可能明确。如果不是直接从声音所属自然人处直接获得音源,需要注意查验相关授权材料和供应方合规证明。声音权利人在签订相关授权协议时,可以通过要求增加音频水印等方式固定权利链条。
(二)肖像权和姓名权
真人转化型和真人扮演型的虚拟偶像的创制都需要以自然人的面部形象、口唇表情和肢体动作为基础,不可避免地触及相关自然人的肖像权保护问题。而真人转化型的虚拟偶像,一般直接使用了真人明星的姓名、艺名等,从而使得相关产出物落入了自然人的姓名权保护范围。
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法典颁布后人格权司法保护典型民事案例之“AI陪伴”软件侵害人格权一案中,案涉软件使用何姓明星的姓名、肖像创设虚拟人物,制作互动素材,将何姓明星的姓名、肖像、人格特点等综合而成的整体形象投射到AI角色上,该AI角色形成了何姓明星的虚拟形象,该行为属于对包含了何姓明星肖像、姓名的整体人格形象的使用,构成对何姓明星姓名权、肖像权和一般人格权的侵害。【5】该案明确了自然人的人格权及于其虚拟形象,给虚拟偶像开发方与“中之人”或其背后对应的真人偶像等各方的权利保护和平衡作出了提醒。
依据《民法典》993条,“民事主体可以将自己的姓名、名称、肖像等许可他人使用”。虚拟偶像开发运营方在使用真人明星、“中之人”等他人形象元素时,应该取得相应的许可,同时严格将使用范围控制在商品、服务和商标等被许可范围内,以避免纠纷产生。
以知名虚拟女团成员“珈乐”休眠及全员“开盒”事件为代表,虚拟偶像因对自然人声音、肖像和姓名使用产生的隐私权、名誉权和个人信息权益纠纷频频出现。下文“‘中之人’的法律问题”一处继续阐述。
三、虚拟偶像的知识产权保护
虚拟偶像的静态形象体现为“图案”,而动态形象又是由“表演”构成的,支撑其动静态形象的底层技术也很是精尖。作为开发者与运营商、广告主或供职单位、内容创作者、真人演员、粉丝和人工智能等多元主体共同建构的结果,【6】它具有智力成果和商誉叠加的性质,天然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对象。
(一)著作权
虚拟偶像的“皮套”与数字艺术作品并无差异,作为美术作品保护在许多判例中都获得了支持。例如,在“米哈游与伊秀网络科技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案【7】中,法院即认为展现虚拟偶像“yoyo鹿鸣”外观形象的作品“以线条、色彩及其组合呈现出富有美感的形象和艺术效果,体现了个性化的表达“”作品符合独创性的要求也具备艺术上的美感,属于我国《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美术作品”。在另一案【8】中,伊秀网络科技未经许可在其运营的手机游戏“妖姬录”的广告宣传中使用米哈游欲进一步开发成虚拟偶像的NOva的形象,法院最终判定伊秀网络科技侵犯米哈游案涉美术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从虚拟偶像开发运营方的角度出发,应当以委托创作或聘任员工等方式合法取得“皮套”的相关权利,与画手等参与“皮套”创作的一方签订明确的知识产权归属协议,并尽早将“皮套”的整体、部分和其他创作元素进行版权登记,并加强侵权线索监控和维权行动。从实际创作的一方而言,可以根据参照IP的知名度和许可费标准与开发运营方商定费用,谨慎签订相关授权、许可使用协议,并在署名等层面充分保证自己的权利。
在“皮套”之外,虚拟偶像的偶像活动可能涉及产生音乐作品、舞蹈作品、文学作品和最常见的视听作品。虚拟偶像开发运营的一方需要通过用户协议、与产出方的协议明确权利归属和使用形式,以免产生不必要的争议。而“中之人”、动画师、编辑、导演和剪辑师则要注意协议中对使用范围的约定,以及最大化争取财产利益。
(二)商标权
虚拟偶像的名称、“皮套”甚至声音元素都可以通过商标权进行保护。例如,“国知局2019年度十大商标异议典型案例”的“洛天依LUOTIANYI”商标异议一案就对虚拟偶像名称及在先权益予以了肯定。在新创华文化诉宅电舍贸易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中,宅电舍贸易告使用的“初音”商标与虚拟偶像“初音未来”商标中的核心主要部分相同且完全一致,构成近似商标,“初音未来”商标具有较高知名度,应给予强保护。【9】
从传统动漫虚拟形象的IP孵化路径来看,作为虚拟形象载体的动画片等获得的经济收益较为有限,开发运营方主要收益来源于衍生品开发。可以预见,未来将在数字媒体、电商平台等网络领域出现更多诸如虚拟偶像“同款”、搬运虚拟偶像图片、视频或者其他蹭热度的侵权行为。作为虚拟偶像的开发运营方,应当在IP孵化的早期就对虚拟偶像的名称、形象等进行全面的商标布局,以为后期偶像活动的开展和衍生品开发奠定完善的权利基础。
(三)邻接权
虚拟偶像区别于传统虚拟形象的关键点之一,就在于其能够进行互动性“表演”,包括直播、唱歌、跳舞和写诗作画等。因此,当下虚拟偶像相关的法律争议也主要集中于其“表演”所涉的邻接权中。在“国内首例虚拟数字人侵权案”的二审【10】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就虚拟偶像Ada的表演者认定和表演权归属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辩,法院最终认定虚拟偶像的相关录像制品中可以包含虚拟偶像形象即对应美术作品的著作权,以及录像制作者权及表演者权,结合著作权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和“中之人”为原告公司员工的事实来看表演者权属于虚拟偶像的开发运营方。
从上述案例体现的司法裁判观点和产业逻辑事实来看,“表演”过程就是“中之人”提供样本和同步数据的过程【11】,虚拟偶像的“中之人”才是其表演活动的实际“表演者”。因此,虚拟偶像开发运营方与“中之人”之间关于权利归属的约定极为关键。由于虚拟偶像的特性,“中之人”几乎不可能行使署名等身份权利,仅能在劳动报酬和肖像等人格要素许可使用费等财产权利层面尽力争取利益。而对于开发运营方来说,应当注意通过与中之人签订劳动合同等明确的协议将“中之人”的“表演”行为固定为“职务表演”,保障自身的利益。
(四)专利权等其他权利
由于虚拟偶像的发展深深倚靠着计算机图形学、图形渲染、动作捕捉、深度学习、语音合成等技术,开发运营商可以考虑通过申请专利并结合商业秘密等方式保护自身权利。例如,腾讯曾经“虚拟演唱会的处理方法、装置、设备、介质及程序产品”【12】专利。而对于其他盗用虚拟偶像形象进行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的行为,更是可以通过提起不正当竞争之诉对自身权利进行保护。
四、“中之人”的法律问题
“中之人”除了“表演”过程中对虚拟偶像活动的人格要素投入和表演行为的权利归属被广泛关注,其“开盒”涉及的人格权问题以及过低报酬引发的劳动争议也时常掀起业内讨论。
(一)“开盒”问题
虚拟偶像的“开盒”是指“中之人”个人身份信息在网络上被公开。“中之人”被“开盒”,意味着自身的个人信息权益、隐私权甚至名誉权等人格尊严受到了威胁。同时,“开盒”对于虚拟偶像的IP孵化也是致命的。因为粉丝买账的是“皮套”所对应的虚拟形象角色,一旦虚拟偶像“开盒”,它的商业周期基本上终止了,等同于真人偶像的“塌房”。
虚拟偶像“开盒”引发的纠纷,已经从网络舆论走向了司法实践。在许某与中视新科动漫网络侵权责任纠纷一案【13】中,NGA论坛是虚拟偶像“新科娘”(心萪)的知识产权权利人,因新科娘的配音及动作捕捉原型许某从该实习岗位离职可能对虚拟偶像的持续运营产生影响,双方产生纠纷,NGA论坛遂发布公告称许某伪造学历骗取工作、泄露公司商业秘密且患有抑郁症,损害公司合法权益。法院最终认为NGA论坛侵犯了“中之人”的隐私权和名誉权,判决公开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为预防“开盒”风险,虚拟偶像开发运营商和“中之人”在签署相关协议时需要特别注意保密条款的约定,并在运营时加强身份信息的保密。例如,可以将“中之人”的身份信息定义为“商业秘密”的范围,并约定与之相匹配的违约责任。
(二)劳动及其他争议
在行业实践中,“中之人”并非都像“国内首例虚拟数字人侵权案”中的“中之人”一样与企业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双方合作和签约的方式是多元的,比如还有劳务关系和经纪关系等。在“首例虚拟主播形象损失纠纷案”中,“中之人”史某与MCN机构苏州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虚拟主播签约合同》,约定由公司为史某提供虚拟形象“乘黄”作为“皮套”,同时提供运营支持和直播平台活动资源。后史某未按约直播,双方产生争议,公司诉至法院。法院最终认定史某违约并向公司支付违约金。
针对因“中之人”与虚拟偶像开发运营商因合作关系而产生的风险,法官同时指出,MCN机构需重视“中之人”权益保障及合规培训,加强“中之人”个人信息安全保障,对符合劳动关系特征的“中之人”及时签订劳动合同,对不符合劳动关系特征的“中之人”通过直播合同等方式明确双方权利义务。【14】
五、虚拟偶像活动合规
在上述“首例虚拟主播形象损失纠纷案”的报道中,法官对于“中之人”言行合规和平台管理同样提出了建议。“虚拟主播应参考真人主播,根据相关行为规范划定自身行为边界,避免虚假宣传、诱导非理性消费、推销假冒伪劣商品、接受未成年人打赏以及散布低俗色情内容等言行。平台应加强管理,对虚拟主播注册进行身份核验、形象前置备案,强化内容治理,对于AI生成内容予以显著标识,如虚拟主播账号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的行为,也应根据其影响程度进行下架、暂停、封禁等处罚,营造清朗的直播环境。”
正如法官所言,虚拟偶像在从事营销类偶像活动时,仍然要同真人偶像一样,遵循《广告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开发运营商作为经营主体要具有相应的行业资质和许可,同时要遵循平台的相关规则和其他行业监管规则。
六、结语
近日,艾媒咨询发布了《2024年中国虚拟数字人产业发展白皮书》。报告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虚拟人带动产业市场规模和核心市场规模分别为3334.7亿元和205.2亿元,预计2025年分别达到6402.7亿元和480.6亿元,呈现强劲的增长态势。【15】虚拟偶像作为虚拟数字人领域内的核心角色,其未来发展无疑是最令人瞩目的。面对行业发展的滚滚浪潮,本文立足于当下虚拟偶像行业实践中的冲突和纠纷,初步探索了虚拟偶像发展面临的法律挑战和保护手段。作为一种具有多元法律性质的商业模式,应将虚拟偶像所涉相关权利视为权利束【16】,从而能“虚中求实”,根据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寻求更为合适的应对之策。
参考文献
1. 初萌:《元宇宙时代的版权理念与制度变革》,载《知识产权》2022年第11期。
2. 蒙晓阳、杜超凡:《虚拟偶像行业中声音侵权现象及其治理》,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10期。
3. 北京互联网法院(2021)京0491民初29341号民事判决书。
4. 北京互联网法院:《全国首例AI生成声音人格权侵权案一审宣判》,载北京互联网法院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_GxGaG6Q2NYHJWQuOtMyrQ,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5月27日。
5. 北京互联网法院(2020)京0491民初9526号民事判决书。
6. 吕菁:《虚拟偶像:多主体建构的超能拟像与元宇宙时代的数字分身》,载《电影新作》,2022年第5期。
7. 广州互联网法院(2020)粤0192民初46388号民事判决书。
8. 广州互联网法院(2020)粤0192民初46388号民事判决书。
9.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2017)浙8601民初3709号民事判决书。
10.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浙01民终4722号民事判决书。
11. 孙山:《虚拟偶像“表演”著作权法规制的困境及其破解》,载《知识产权》2022年第6期。
12. 专利公开号为CN114120943A。
13. 北京互联网法院(2020)京0491民初17175号民事判决书。
14. 江苏高院:《二次元虚拟主播“擅自罢工”,公司损失怎么算?》,载江苏高院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zIhSLhpkq5wTBmsSBmrbDA,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5月29日。
15. 艾媒咨询:《2024年中国虚拟数字人产业发展白皮书》,载艾媒咨询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dsmwjsQoGvRi2d2BJVgb3w,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5月29日。
16. 吴镱俊:《虚拟偶像著作权保护的域外经验与我国应对》,载《青年记者》2023年3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