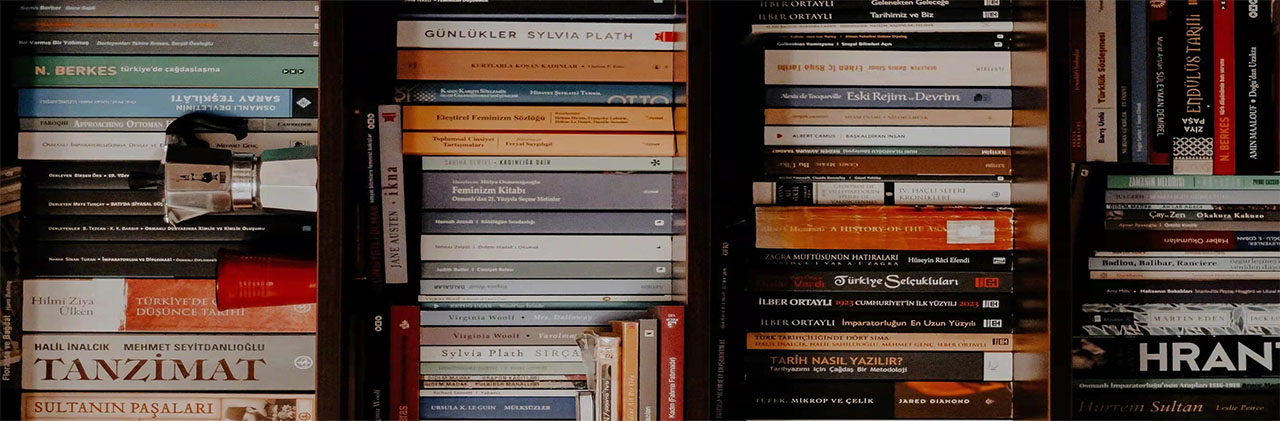
作者:
上海天聿格(北京)律师事务所 郭永莹律师
上海天聿格律师事务所 刘曦璟律师
摘要:本文聚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著作权保护问题,深入探讨其面临的困境、成因及解决路径。研究难点在于非遗与著作权保护在多方面存在本质差异,导致确权、行权、维权困难。困境表现为确权门槛高,因非遗与著作权保护特性差异,使确权环节模糊;行权环节缺失,现行法律对权利主体行权规定不明;维权难度极大,非遗创作素材特性致独创性质疑及判赔低。困境成因包括价值冲突致立法滞后、司法裁判支持有限、独创性及作品认定等要求严格、版权法律救济能力不足。对此,应加强法律解释与适用,完善著作权制度并设专门机构管理;强化司法保护,明确裁判标准、提高判赔;选用多元救济,如商标注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总之,非遗著作权保护复杂,当前立法与司法滞后,需多元保护路径构建全方位保护体系。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著作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著作权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简称“非遗”(以下均称“非遗”),与“物质文化遗产”相对,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下称《公约》)中首次提出并正式对非遗进行定义,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下称《非遗法》)作出的界定与《公约》基本一致,同时《非遗法》第二条对非遗的形式进行了列举:“包括:(一)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二)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三)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四)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五)传统体育和游艺;(六)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遗对人类社会的价值巨大。在农业经济时代主要体现为“使用价值”,在工业经济时代则具备了“经济价值”。迈入知识经济时代,非遗更是“文化价值与使用价值并存”。这使得非遗有了财产权保护的利益基础。虽然对于非遗财产权的保护历来有公权保护以及公私权保护相结合的诸多争议,但知识产权尤其是著作权作为非遗经济利益的有效保护方式在司法实践中已并不鲜见。利用非遗技法创作出来的具有独创性表达的作品落入了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一般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下称《著作权法》)第六条所规定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随着“知识产权保护逐渐内化为民俗传承者自身行为”,著作权保护对非遗传承发挥的作用更为突出,但是相关权利主体的确权、行权和维权实践往往遇到较大挑战。
本文从非遗著作权保护面临的困境出发,分析困境产生的原因和实践表现,最终从立法、司法角度为权利实现寻找适宜路径。
如前所述,在当今文化保护的大格局下,著作权保护已然成为非遗保护的一种主流方式。然而,深入探究便会发现,基于非遗自身独特的性质、著作权保护的既定范围以及当前法律体系的设计,并非所有的非遗都能够顺利地纳入著作权保护的范畴之内,这一现状在诸多方面都有着明显的体现。
首先,非遗和著作权保护的目的存在本质性的差异。从非遗保护的角度来看,其目的明确地被界定为“继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加强对非遗的“保护、保存”工作。正如《非遗法》第一条所规定的:“为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制定本法。”这清晰地表明,非遗保护的重点在于对历史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发掘,全力防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灭失或失传,其核心是维护公共历史文化的传承,着眼于整个民族文化的长远发展和延续。而著作权保护则有着截然不同的侧重点,它主要是为了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具有强烈的私权属性,更侧重于对创作者个人权益的保护,通过赋予创作者一定期限内的专有权利,激励其进行创作活动,推动文化和知识的创新与传播。这种目的上的差异,使得非遗在寻求著作权保护时,面临着根本性的理念冲突。
其次,非遗和著作权保护的内容也有着显著的不同。非遗的保护范畴极为广泛,它不仅涵盖了那些符合著作权法定义的“作品”或者“表演”,还包括了诸如“技艺、医药、历法和民俗”等众多独特的领域。以传统技艺为例,许多非遗技艺经过世代传承,形成了独特的工艺和制作方法,这些技艺所产生的作品或表演,只有在具备独创性的前提下,才能够通过著作权进行保护。然而,非遗技艺本身以及处于公有领域的传统知识,由于其历史悠久、来源广泛,难以满足著作权法对独创性的要求,因此并不能通过著作权得到有效的保护。这就导致了大量的非遗内容被排除在著作权保护的范围之外,使得非遗在寻求法律保护时面临着内容上的限制。
再者,非遗和著作权保护的手段也存在明显的差异。非遗的保护方式包含了更多“认定、记录、建档”等公权力措施。政府部门在非遗保护中发挥着主导作用,通过组织专家评审、认定非遗项目,对非遗进行详细地记录和建档,以及开展各种保护活动等方式,确保非遗的传承和发展。而著作权保护则主要依靠法律赋予作者的专有权利,通过作者自行行使权利或者授权他人使用作品来实现保护。这种保护手段的差异,使得非遗在利用著作权进行保护时,难以找到与之相匹配的操作模式。
最后,非遗和著作权保护的期限也截然不同。著作权具有一定的期限限制,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作者享有对作品的专有权利,期限届满后,作品便进入公有领域,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使用。而非遗则致力于对公共历史文化的永久保护,它承载着一个民族的记忆和智慧,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需要得到长期的传承和发展。这种期限上的差异,使得非遗在寻求著作权保护时,面临着保护期限不匹配的问题。
正是由于上述诸多方面的差异,能够通过著作权保护的非遗形式相当有限。在版权登记、作品发表和合同约定等确权环节,非遗作品更容易产生模糊地带。以版权登记为例,由于非遗的创作主体往往具有群体性和传承性的特点,难以确定明确的作者,这就给版权登记带来了困难。此外,传承人认定、名录申请等非遗特色“确权”标准和后续扶持政策在各地并不统一,这也导致并非所有非遗作品都能够受到非遗的专门保护。这些问题的存在,给非遗作品的后续行权、维权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确权困难是导致非遗行权环节缺失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非遗在确权方面存在诸多难题,非遗传承人等权利主体往往无法主动行使权利,对外授权他人使用非遗作品。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非遗保护的责任主体主要落脚于国家、政府和各级文化主管部门等。法律为这些主体设置了扶持、开发等义务,鼓励他们采取各种措施促进非遗的保护和发展。然而,对于非遗权利主体如何行使权利,或者是否需要设立相应的管理组织来行使权利,法律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这就使得非遗权利主体在面对商业化活动时,缺乏直接的法律依据和操作指引。
例如,一些非遗传承人拥有独特的技艺和作品,希望能够通过与企业合作进行商业化开发,将非遗推向更广阔的市场。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他们在与企业签订合作协议时,往往会面临诸多问题,如权利的归属、授权的范围、收益的分配等。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不仅会影响非遗传承人的积极性,也会阻碍非遗的商业化发展。此外,由于缺乏相应的管理组织,非遗权利主体在面对侵权行为时,往往难以形成有效的维权合力,导致侵权行为得不到及时地制止和惩罚。
非遗创作以传统历史文化元素为基础,这一特点在后续维权过程中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由于非遗创作的素材大多来源于公共领域的传统知识和文化元素,在维权时势必会受到独创性方面的质疑。侵权方往往会以非遗创作缺乏独创性为由,对创作者的权利基础提出挑战,使得创作者的维权风险大大增加。例如,一些传统民间故事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后,原故事的传承人和创作者在维权时,往往会面临侵权方以故事来源于公有领域为由的抗辩,这给维权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另外,目前司法实践中知识产权案件整体判赔水平也对非遗维权产生了不利影响。即使非遗创作人能够顺利维权,所获得的赔偿与他们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和投入的维权成本也难以匹配。在一些非遗侵权案件中,侵权方通过非法使用非遗作品获得了巨额的经济利益,而创作人却只能获得微薄的赔偿。这种不合理的赔偿机制,使得作者的维权意愿不高,进而导致侵权行为愈发猖獗。一些不法分子正是看到了非遗维权的难度和风险,才敢于肆意侵犯非遗权利主体的合法权益。
著作权保护的价值与非遗价值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和冲突。具体体现在:第一,著作权保护私权价值,而非遗具有公有性。非遗作品中蕴含的历史文化元素早已进入公有领域,不仅任何人有权自由利用,且广泛的利用实际更有利于相关内容的传播和传承。将公有领域的内容纳入著作权规制的范畴,有违基本的法理。第二,非遗文化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很多情形下无法轻易地明确作者,导致著作权保护无法适用。第三,非遗文化的传播依赖于广泛的参与,著作权法的介入虽然规范了商业化利用环节,但不可避免地抑制了相关内容的自由流转。上述根本性矛盾的存在,使得我国对于非遗相关的著作权立法相当谨慎。尽管自1990始便在著作权法律中明确提及“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适用专门的法律规范,相关的细则却迟迟未出台。2011年6月1日施行的《非遗法》和2013年7月18日修订颁布的《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均侧重于行政手段规制。《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对于非遗民间文艺作品的权利内容、授权机制、改编作品授权和利益分配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划,但自2014年9月2日对外征求意见以来,产生了是否能够利用著作权法保护、权利主体、作品的精神权利保护、财产权利保护及公有领域保护等方面相当多的争议,以至于至今尚未正式颁布施行。因此,非遗作品迄今尚无具体明确的著作权保护依据,确权、行权困难重重,只能依据《著作权法》的基本规定寻求事后救济。除了作品本身保护依据的缺失,目前的法律法规也无法清晰解释非遗传承人利益保护和作品本身经济利益保护的竞合问题,亟待更进一步研究。
具体法律依据的缺失进一步造就了司法裁判尺度过紧,适用著作权法保护的举证难度相当高,维权困难重重。
非遗作为公共文化内容的属性,使得其独创性判定中“独立完成”部分始终受到质疑。而非遗艺术创作者的对于作品“创造性”的理解与著作权法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客观差距。因此非遗作品是否具有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独创性,是每一个维权案件的基本挑战。在洪福远、邓春香诉贵州五福坊食品有限公司、贵州今彩民族文化研发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中,双方就案涉作品是否具有独创性产生了争议。被告认为,案涉作品中的鸟纹、如意纹、铜鼓纹均源于贵州黄平革家蜡染的“原形”,原告作品中的鸟纹图案也源于贵州传统蜡染,这些元素都是传统的非遗元素,原告涉案作品并不具备独创性。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洪福远从事蜡染艺术设计创作多年,先后被文化部授予“中国十大民间艺术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2009年8月其创作完成的《和谐共生十二》作品发表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福远蜡染艺术》一书中,该作品借鉴了传统蜡染艺术的自然纹样和几何纹样的特征,色彩以靛蓝为主,描绘了一幅花、鸟共生的和谐图景。虽然对传统元素有所借鉴,但该作品对鸟的外形进行了补充,对鸟的眼睛、嘴巴丰富了线条,使得鸟图形更加传神,对鸟的脖子、羽毛融入了作者个人的独创,使得鸟图形更为生动,对中间的铜鼓纹花也融合了作者自己的构思而有别于传统的蜡染艺术图案,具备独创性,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除了独创性,非遗元素只有具备具体的载体和表现形式,才能作为作品保护。这是除了涉非遗作品外,其他著作权案件一般不会遇到的难题。在获得支持的著作权维权案例中,案涉作品均有出版物、视频作为具体载体,甚至尝试通过外观设计专利权申请和著作权登记等方式固定权利基础。如果只是传统戏剧、民俗和体育等传统知识的表达,不能认定为作品。
“中国非遗保护第一案”,即贵州省安顺市文化局与导演张艺谋、制片人张伟平及出品方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署名权纠纷一案,便体现了非遗作品认定的困难。案件起因于张艺谋执导的电影《千里走单骑》中,将安顺市独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安顺地戏”错误地标识为“云南面具戏”,且未在影片及公开场合明确其真实身份,引发安顺市文化局的不满与诉讼。安顺地戏作为拥有600多年历史的民间戏剧,被誉为“中国戏剧的活化石”,并被列入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5年,电影《千里走单骑》热映,影片以“云南面具戏”为线索贯穿始终,但实际上,该“面具戏”的表演内容、演员、面具等均来源于安顺地戏。安顺市詹家屯的詹学彦等8位地戏演员受邀参与了影片的拍摄,但影片上映后,却未对安顺地戏的真实身份进行明确标注。本案的焦点在于安顺地戏是否享有署名权以及电影《千里走单骑》是否侵犯了安顺地戏的署名权。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认为,署名权是作者表明其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安顺地戏作为一个剧种,是对戏剧类别的划分,而非对于具体思想的表达,因此不构成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也不享有署名权。历经1年零4个月的审理,2011年5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安顺市文化局的全部诉讼请求。法院认为,虽然安顺地戏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受法律保护,但影片《千里走单骑》将安顺地戏作为一种文艺创作素材进行使用,并未产生法律禁止的歪曲、贬损或误导混淆的负面效果,且被告主观上并无侵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故意和过失。因此,法院判决原告败诉。
而在邱某某诉李某某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中,原告使用非遗技艺“侧烧”制作了“建盏”,不仅通过视频发布了该作品,还进行了著作权登记,并申请了外观设计专利。该传统手工技艺品因技艺创新而具有独创性的表达,且具备美术作品的审美意义及艺术创作高度,可以作为美术作品予以著作权保护。在梁季兰与龙口市北马王堃百货店等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中,原告根据传统非遗元素,创作了大量团扇纹样,并出版了图书。尽管被告主张类似纹样自古就有,图书作为美术作品的载体,使得法院最终认定上述团扇纹样可以受到著作权保护。
多数判决都体现了极高的作品比对要求,只有各方面“基本一致”“完全一致”的情形下,才构成“实质性相似”,认定侵权。
南京云锦研究所有限公司与南京宜贡坊云锦织造厂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中体现了这种严格尺度。该案原告南京云锦研究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云锦公司)提交的1977年7月《牡丹写生资料》中“万紫千红”作品的创作者是朱某,朱某系其单位员工。南京云锦公司认为,其系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南京宜贡坊云锦织造厂(以下简称宜贡坊织造厂)未经许可制作、销售被诉侵权云锦侵害了其作品著作权。宜贡坊织造厂提供苏作登字-2013-F-00017896云锦之牡丹系列作品,用以证明其享有涉案被诉侵权云锦作品的著作权。“万紫千红”作品在被诉侵权云锦登记前已经被制作为云锦礼品被赠送,作为云锦产品被销售以及参展并获奖。法院认为,南京云锦公司“万紫千红”云锦作品和被诉侵权云锦经比对,两者在局部色彩、个别花瓣和花蕊的造型方面稍有差别,但整体看来表达的方式和内容基本相同。制作过程中使用的如“金宝地”等生产工艺,再现了美术作品的表达。宜贡坊织造厂侵害了南京云锦公司对涉案作品所享有的复制权、获得报酬权以及相关的人身权等权利。云锦的生产工艺主要包括纹样设计、挑花结本、造机、原料准备、织造五个部分。在云锦作品的创作过程中,相关阶段的创作成果如白描作品、上色作品以及运用“金宝地”等工艺创作完成的云锦产品,受到著作权法保护。作为南京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云锦作品的创作是一个传承和创新发展的过程,创作中可以适当借鉴已有成果,但是必须具有自身构成独创性表达的部分,符合著作权法作品独创性的要求,才能获得著作权法的保护。并且原创产品和侵权产品在生产工艺、整体表达方式和内容上“基本相同”,才最终认定为侵权。
在另一类案南京云锦研究所有限公司与南京宜贡坊云锦织造厂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中,法院更是在实质性相似的审查中,仔细比对了各种元素的相对大小、相对位置、排列布局、整体形态、视觉效果、色彩处理,最终认定宜贡坊织造厂侵害了南京云锦公司对涉案作品所享有的复制权、获得报酬权以及相关的人身权等权利。
而对于市面上更为普遍的情况,侵权作品抄袭原创作品基本设计但并未达到视觉效果一致,则无法获得司法裁判的支持。
上述司法裁判表明,非遗的特殊性使得通过著作权保护遭遇了较多困难。目前对于相关内容是否具有独创性、是否具有作品载体以及公有元素的使用和表达是否相似,司法裁判的认定尺度严格。在此种情况下,一些案件是通过其他权利基础进行保护的。
例如,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保护。在“非遗”传承人王增世诉某购物平台和平台店铺商家文某肖像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中,被告利用非遗传承人的形象和影响力进行销售宣传,最终被判定侵权。原告王增世享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医药(骨伤蛇伤疗法)传承人”荣誉称号,是雷山县域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苗医药的代言人2022年,王增世发现江西某“祖传秘方土方生发液”的店铺在某知名电商平台上销售的一款生发育发产品,在商品详情页面上大量使用了自己的肖像,并配有自己接受采访以及进行诊疗技术传授等图片。图片上还标注了“自家医药、传承百年”“祖传防脱生发养发”等字样。原告并未授权任何人以自己的名义生产、销售除骨伤蛇伤苗医药以外的产品,最终法院认定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肖像权,并构成了不正当竞争。
此外,通过将非遗符号注册为商标的保护方式在实践中大量存在。非遗符号往往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特色。将这些符号注册为商标,不仅可以为非遗项目提供法律上的保护,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非遗文化的传播和发展。通过商标注册,非遗项目能够确立其独特的品牌身份,增强市场竞争力,同时也有助于防止他人滥用或盗用非遗符号,从而维护非遗项目的合法权益。例如,湖南湘西注册了“古丈毛尖”的制作工艺属于非遗,并且已经注册地理标志商标。
在非遗的法律保护体系中,著作权保护是极为重要的一环,但目前在实际应用中,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依据,导致司法保护在非遗著作权保护方面显得力有不逮,难以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进一步加强相关细则的制定工作迫在眉睫。
在完善著作权法律制度方面,可以从狭义著作权和邻接权两个关键方面分别入手,全面推进相关工作的开展。
首先,针对狭义著作权部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条例》的出台对于完善非遗著作权保护法律体系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非遗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已经在《著作权法》中进行了明确规定。尽快针对争议部分开展研究,加快推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条例》的出台,明确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归属、权利内容、保护期限等关键问题。同时,尽快成立条例中所提及的由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专门机构,负责对相关财产利益分配进行管理,也是十分必要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往往涉及众多的创作者和传承者,其财产利益的分配问题较为复杂。如果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很容易引发利益纠纷,影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传承与发展。通过成立专门机构,建立科学合理的财产利益分配机制,能够确保利益分配的公平、公正、合理,激发创作者和传承者的积极性。此外,增加精神性权利保护与著作权法的衔接性规定,对于充分保护非遗的精神价值具有重要意义。非遗不仅具有经济价值,更具有深厚的精神文化价值。在一些案例中,某些企业在使用非遗元素进行商业宣传时,对非遗进行了不当的解读和利用,损害了非遗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和民族情感。因此,在著作权法中增加精神性权利保护的相关规定,明确非遗权利人的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精神性权利,能够更好地保护非遗的精神价值。
其次,针对邻接权部分。从非遗的演绎特性出发,将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中固定形态的作品视为著作权法中的邻接权客体,是一种可行的保护思路。在立法操作层面,可在著作权法的邻接权部分增设一项新的邻接权,专门对非遗尤其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版权内容与权利行使规则进行设计与规定。邻接权的主体应明确为传承人,因为非遗的活态保护离不开传承人,他们的艺术实践既包含继承又有创新。传承人通过自己的表演、展示等方式,将非遗作品传承和发展下去。通过邻接权制度确认与保护传承人的艺术实践,能够为非遗传承创造良好的传衍法律环境。
对于作品的传播者,鉴于其在作品传播利用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也应给予其传播者权利来保护其利益,以促进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广泛传播。例如,一些文化传播公司通过举办非遗展览、演出等活动,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推向更广阔的市场,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非遗。如果传播者的权益得不到保护,他们的积极性将会受到打击,不利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传播与推广。
此外,还需加强《非遗法》等行政性质法律法规与著作权制度的衔接,形成更为完善的法律保护体系。《非遗法》主要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对非遗进行保护,而著作权制度则侧重于从民事权利的角度对非遗进行保护。两者在保护非遗方面各有侧重,但也存在一定的交叉和互补。通过加强两者的衔接,能够实现对非遗的全方位、多层次保护,确保非遗在不同法律领域都能得到有效保护。
目前,非遗法律适用难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非遗的法律保护工作。因此,进一步强化司法保护力度势在必行。司法保护作为非遗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其作用的充分发挥对于维护非遗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打击侵权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司法机关应明确裁判标准,制定清晰、统一的裁判规则,使非遗相关案件的审理有明确的依据。在非遗侵权案件中,由于缺乏明确的裁判标准,不同地区、不同法院对于同类案件的判决结果可能存在较大差异,这不仅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也让非遗权利人在维权过程中感到无所适从。例如,在判断非遗作品是否构成侵权时,对于 “实质性相似” 的认定标准不够明确,导致一些侵权行为得不到应有的惩处。因此,司法机关应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制定司法解释等方式,明确裁判标准,统一裁判尺度,为非遗相关案件的审理提供明确的指引。
同时,要提高判赔水平,对于侵犯非遗权益的行为给予严厉地惩处,通过提高侵权成本,有效遏制侵权行为的发生。在一些非遗侵权案件中,由于判赔金额较低,侵权人所获得的利益远远高于其侵权成本,这使得一些侵权人敢于铤而走险,不断侵犯非遗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司法机关应根据侵权行为的性质、情节、后果等因素,合理确定判赔金额,提高侵权人的侵权成本,让侵权人付出应有的代价。例如,对于故意侵权、多次侵权的行为,应加大判赔力度,以起到震慑作用。
此外,司法机关还应加强与其他部门的协作配合,形成保护非遗的合力。在非遗保护工作中,司法机关应与文化、文物、市场监管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案件移送、联合执法等协作机制,共同打击侵犯非遗权益的行为。例如,文化部门在发现非遗侵权线索后,应及时将相关信息移送司法机关,司法机关应依法进行查处;市场监管部门在市场巡查中发现侵权产品,应及时予以查处,并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通过加强协作配合,能够形成保护非遗的强大合力,有效维护非遗的合法权益。
在非遗维权过程中,权利人应适时运用商标和不正当竞争等多种法律手段对权利进行保护和救济。单一的法律保护手段往往难以满足非遗保护的实际需求,因此,选用多元救济方式,能够拓宽非遗保护的法律途径,为非遗权利人提供更加全面、有效的保护。
通过商标注册,将非遗的标识性元素进行商标化保护,防止他人恶意抢注和侵权使用。非遗的标识性元素,如传统技艺的名称、图案、标志等,具有较高的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如果这些标识性元素被他人恶意抢注为商标,将会对非遗的传承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例如,一些地方的特色小吃、传统手工艺品的名称被他人抢注为商标,导致当地的非遗传承人无法正常使用这些名称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因此,非遗权利人应及时将非遗的标识性元素进行商标注册,取得商标专用权,以防止他人恶意抢注和侵权使用。当然,不得不说明的是,非遗产品一般注重传承与手工艺价值,所以并非所有的非遗产品都愿意通过添加商标或LOGO的方式进行保护,甚至一些消费者也会青睐于没有额外商业标识的手工艺品,以实现其收藏价值或独特性。笔者认为,如在合适位置或者隐蔽的位置添加标识性元素,则可以在有争议的时候起到证明来源的作用,防止他人侵权。
在面对不正当竞争行为时,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维护非遗在市场竞争中的合法地位和利益。一些企业为了获取不正当利益,在市场竞争中采取假冒非遗产品、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手段,损害了非遗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例如,一些企业在产品包装上标注虚假的非遗标识,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误以为其产品是正宗的非遗产品。非遗权利人可以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对这些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维权,维护非遗在市场竞争中的合法地位和利益。
综上所述,非遗法律保护路径的完善与选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加强法律解释与适用、强化司法保护力度、选用多元救济方式等多个方面入手,全面推进非遗的法律保护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非遗的传承与发展,让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1.李志恒:《商标、非遗与知识产权——一个从当代司法实践出发的民俗学讨论》,载《民间文化论坛》2024年第1期。
2.聂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及其边界研究》,载《文化遗产》2023年第3期。
3.聂鑫:《制度理性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财产权保护研究》,载《文化遗产》2021年第4期。
4.罗宗奎:《非物质文化遗产商标保护的实践、问题和对策》,载《文化遗产》2020年第2期。
5.施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间文艺作品著作权保护的内在矛盾》《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8期。
6.黄玉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权保护》《中国法学》2008年第5期。
1.李卓谦、刘国彬、陈丽娜:《以法治之光照亮“非遗”保护之路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法保护的雷山实践》,载“民主与法制”公众号2025年1月23日,访问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amp=1738343214&ver=5784&signature=KlYYJ2yA17lvgU2GQW*vBJhWYKWjsxojV0IVCgqcRP3A0Ivx2CXEiEe0qsYcrGRkdiPsckdXApqnXytqiwqeY1MyTg36BnwQCZvIpjd8J4noCFSp57-WF6RAL60FLBRH&new=1,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1月23日。
2.福建高院:《2023 年度福建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例之八》,载“福建高院” 公众号 2024 年 4 月 29 日,访问链接: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ODMyOTQ2Mw==&mid=2653375546&idx=2&sn=965c368e59f06d48326b7a55cfe61a3b&scene=0,最后访问日期 2025 年 2 月 1 日。
3.南京中院:《发布丨南京法院中华传统文化领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载“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众号2023年7月10日,访问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aUlN5CNL8iOgfvi3aLZ1Pg,最后访问日期 2025 年 2 月 1 日。
4.北京互联网法院(2020)京 0491 民初 1886 号民事判决书
5.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筑知民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书